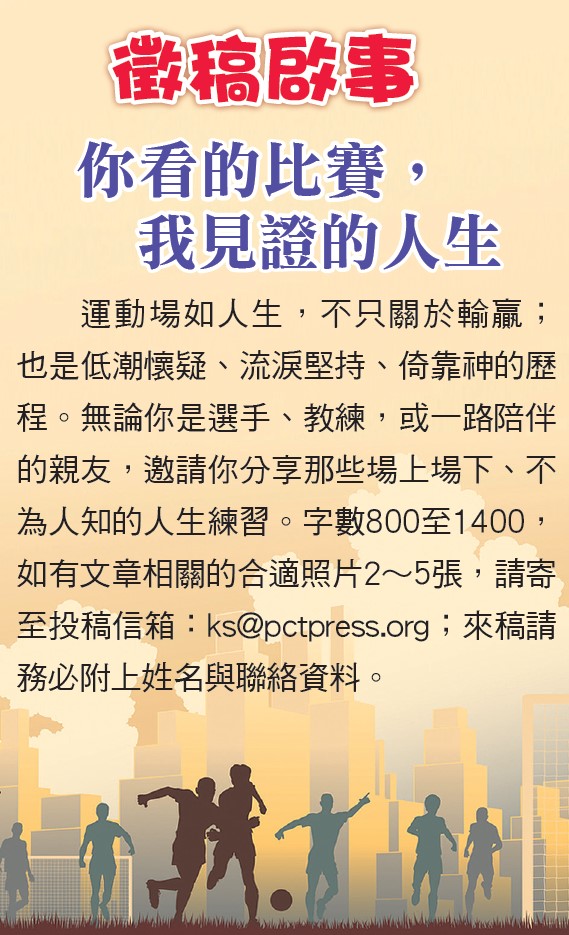2025年2025年9月14日第1515期【翻山越嶺找回你】
〈本週焦點〉祂愛你,就愛到底
〈信心加油站〉歸途的名字叫拔馬
〈幸福光點〉尋回本來的面目
◎Vukin Takalomay(拔馬部落青年)
我回來了,回到那塊從未真正踏上的土地。拔馬,一直在我心裡沉睡。如果沒有我的大伯買文男、我的姊姊買欣鳳,沒有左鎮教會的大家接納與照顧,我大概永遠都不會成為拔馬部落的男人。
從小,我的記憶在雲林開展,生活的每一個細節,都與原鄉無關。但我總記得,我的阿嬤姓買,也總記得家人說過:「我們好像有原住民的血統。」說完就不了了之。
直到大學讀中文系,因與某次準備許久的實習機會擦身而過。在面對未來的迷惘中,我深切禱告:「主啊,祢到底要我做什麼,可不可以告訴我?」
心底的聲音,帶我回家
後來我選擇留在學校實習,過程中,對於自己「原住民」身分的好奇與模糊想像,驅使我不斷搜尋:「台南 原住民」、「原住民 買姓」……,這些關鍵字開始占據我的演算法。某天我點進了一則新聞寫著: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更審:原住民身分為與生俱來,並非國家恩賜。」
那一刻,心底有個聲音被喚醒。
「為什麼身分需要訴訟?」
「我們的文化與語言在哪裡?」
「我的部落呢?」
我開始驅車南下,前往一個又一個與西拉雅文化相關的場域。我渴望找到答案,卻發現問題越問越多。直到我再次被一個演算法打中,彈出了一個活動頁面「Musuhapa西拉雅學校」。
這個營隊讓我第一次真的碰觸到語言與文化,西拉雅族與長老教會、甚至基督教的深切關係,也讓我明白回家的路原來這麼長。
第一年學族語,困難如山。我曾打開教材,卻讀不懂也記不起來,一度想要放棄,覺得「學過就好」。但某天我這樣問自己:
「你的西拉雅,是什麼樣子?」
「你想成為怎樣的西拉雅族人?」
於是,隔年我再次走進族語師資培訓課程。這次我撐住了,學得比第一年更深,也再度向神禱告:「主啊,祢要我做這件事的話,我願意,但我需要主祢幫我把路安排好。」
培訓結束後,剛好接到一個重要的消息:「Vukin,你要不要來參加原民台的族語媒體人才培訓?這些族語主播即將退休,我們除了需要培訓一批新的族語主播之外,我們想讓平埔族群有自己的聲音。」
我答應了。雖然沒有經驗,仍一頭栽進媒體訓練的密集課程。在實習現場裡,我真正體會語言的力量,也重新認識了自己。那些日夜趕稿、現場採訪、即時翻譯的日子,成為我文化認同的一部分。
結訓後,我成為一名族語老師。孩子的眼睛、語言的遞送,讓我更清楚知道:語言不是知識,而是活著的痕跡。但我也看到孩子國小畢業後,沒有繼續學習的空間,語言又再一次斷掉。那一刻我告訴自己:「我不願它就這樣消失。」
我開始到處授課,到哪裡都說西拉雅語;不論城市或鄉村,只要有人需要,我就去。這不只是教學,而是一種呼召。
但我心中仍有一個更深的召喚:我想回部落生活。我問家人:「我們的老家在哪?」他們說不清楚,因此我打通了大伯的電話,慶幸他還記得那個地點。當我回到老家,第一次見到從未謀面的家人,大伯語重心長地說:「尋根是好事,但不要三分鐘熱度。」
我聽懂了。因為不想被長輩看低,我翻閱文獻、回到教會、開始學著如何生活;不是訪客的生活,而是進入部落的時區、學習部落的規則。我也暫居在大伯的老屋,那是我第一次,真正以一個拔馬青年的身分,回到這片土地。
我們一起,把部落點亮
2024年,我開了一家LawLaw嘮嘮咖啡廳。這不只是一間店,而是一個聚點,是願意留下的年輕人共居、共享的地方。我也成立「歸途拔馬青年小組」,希望接住那些像我一樣,半路才找到家的青年:只要你願意回來,這裡就有一盞燈。
拔馬只有一點光,但我相信,如果我們一起走,就能慢慢把整個部落點亮。這條回家的路不是觀光,而是呼召。它是成為自己,透過擺上,透過群體前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