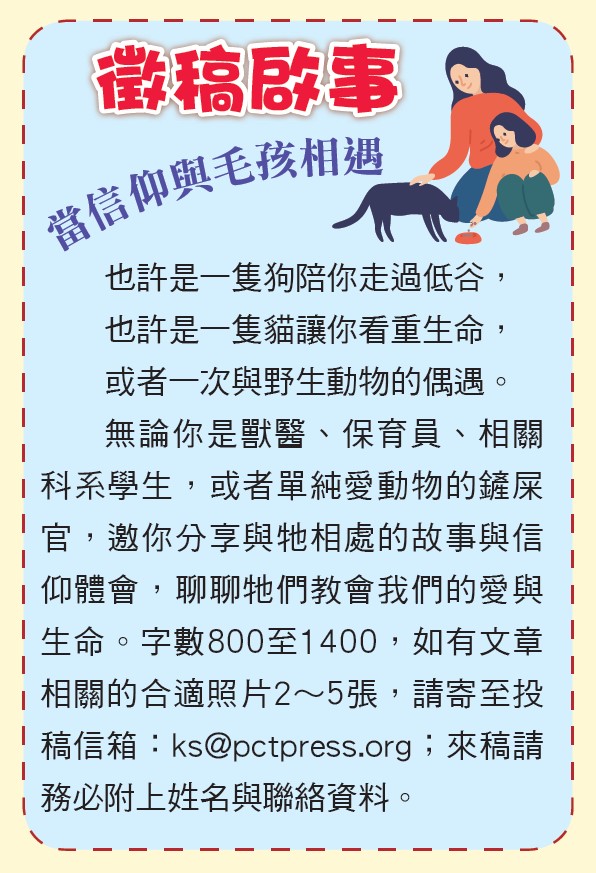2025年6月8日第1501期【 名字的所在】
〈本週焦點〉重新擁抱自己
〈信心加油站〉忘記了姓名的請跟我來
〈幸福光點〉在不能奔跑的身體裡
◎Padaug Tikutung(神學生)
長輩們曾告訴我:「咱是平埔族!西拉雅的!」然而,關於文化與語言,我卻什麼也不知道。因著台南市定原住民的註記,我從戶政單位找到日治時期戶口名簿中的種族註記,上頭寫著「熟」,確認祖父母家族皆為「熟番」。
也有家人告訴我,祖先是從中國移民來的,這讓我對身分產生極大的懷疑,也不斷要求自己一定要說「台語」。我不停問自己:「我到底是誰?」為什麼關於自己所屬的族群,心中竟有這麼大的矛盾?語言是溝通的工具,為什麼只能說台語?我們是西拉雅族,現在也有老師教族語,為何不能好好學、好好說?
族裡尋根,在內心深處發芽
進入神學院之前,我曾在鄒族的小學擔任代課老師,也兼任行政,因而有許多機會接觸社區、學習文化。一開始最常被問兩個問題:妳是哪一家的孩子?以及,妳是哪一族的?起初我總是帶著害怕的語氣,回答自己是西拉雅族人,後來才逐漸顯得自然。雖然我不斷接觸並學習鄒族的語言與文化,對於西拉雅族的一切,始終不敢正視。在部落與教會,長輩們經常講述鄒族的歷史,也談起鄒族與西拉雅族之間的故事,有一股力量悄悄推著我去尋找「我是誰」。
2009年是特別的一年。年初,台南縣開始受理日治時期戶口名簿種族欄註記為「熟」的平地山胞,補登記為原住民;我和家人也在此時完成登記。那年暑假,我參加了西拉雅語言營,對西拉雅的文化與語言產生好奇。但營會結束後,我始終不敢再觸碰這些,只是將那顆種子深埋心中。直到與鄒族的相遇,這顆種子才逐漸生根。後來入讀台南神學院,牧師們也鼓勵我去認識自己,尋找兩個族群的特色,我終於看到那顆種子發芽。2022年初,在一場聚會中,我得知《拉丁文蕃語字簿》記錄了許多西拉雅族的姓氏,我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家族名,這顆種子的根,也從此在我心中越扎越深!
西拉雅族共有四大社:新港社、目加溜彎社、蕭壟社及麻豆社。目前位於台南市玉井區的西拉雅族人,多為新港社後裔。新港社歷經數次遷徙,其中一支族人來到台南山區。透過長輩述說家族遷徙史,我才知道我們是屬於新港社的族群。
每一社的個性略有不同,像麻豆社的族人個性較為剛烈,新港社則較溫和。有位牧師對我說:「多去和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接觸、對話,可以刺激並幫助妳找回語感和文化。」在與他族對話的過程中,我發現新港社族人的性格與鄒族人相似——內斂、溫柔又寡言。鄒族的長輩也與我分享,玉井、左鎮、岡仔林一帶過去是E’ucna(溫)家的獵場。從這些對話中,我意識到過去的生活其實有著許多交集。
當我開始閱讀文獻與聆聽口述歷史,探索西拉雅文化及與其他族群的互動,發現原來地瓜酒不只是鄒族的文化產物,西拉雅族也有;鄒族的kuba和西拉雅的kuva,皆為政治、宗教與社會運作的核心,及鄒族人曾說西拉雅人是「追鹿的人」等。這些發現激發了我的好奇心,讓我對語言與文化的學習產生更深的動力。
回家路,認同與學習的旅程
我參與原住民信仰扎根營「字.覺」,目的就是要找回「我是誰?」但在過程中,心中也充滿矛盾、掙扎與疑問,甚至經歷衝撞。或許是因為祖先曾在壓迫的時代中,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「做自己」;但我仍有機會,一步步建構對族群的理解與認同,重新認識自己的根。雖然我們的族群失去了許多東西,但荷蘭時期留下的新港文書,幫助我們找回語言;感謝族人保留文化慶典,使我們如今能重新擁抱那被找回的記憶,並由衷喜歡與認識自己的文化與語言。
尋找身分認同與認識自己的文化,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。在這條路上,我們需要一群人一起前行,為著共同的目標努力。認同的歷程,必須是「發自內心的」,而非消費自身或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化。雖然這條路困難重重,學習也永無止盡,但要學會重新擁抱那被喚醒的身分,也是一種必修的功課。